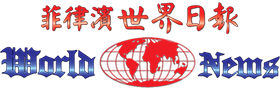第12版:廣場

本版標題導航
日期
當前報紙日期: 2019-04-08
清明,敬娘一座糧倉
高懷昌
2019-04-08
“清明麥埋老鴰高,心緒牽念似柳搖。又是一年祭祀時,滿目蔥蘢起綠滔”。這首《清明心緒》,記述著我搖柳般的紛亂心緒,為啥?因一夢。
去年秋后的一天,與文友騎車至一村莊,見村民門前堆放著很多玉米穗,金燦燦很是喜人,便說,看現在玉米多得賣都沒處賣。沒想到此后不久,便夢見娘沒吃的了。夢境中好像是在娘住處,仿佛娘在干活兒或是在吃飯,反正很模糊、很疏離、很縹緲,無法親近如生前母子,無法辨清娘在干啥,但一點很清晰:娘沒吃的了。於是醒來兩眼淚汪汪。
娘生於貧苦,長於貧苦。在飢寒交迫的舊社會,在水、旱、湯(指軍閥湯恩伯)、蝗“四大害”施虐的豫北大地,在日寇進犯、土匪四起的年月,娘記憶最多的就是逃離日本人、逃離土匪。一見有日本鬼子或土匪來了,就四散而逃,可謂提心弔膽,命如螻蟻。娘從小就沒了父母,1946年25歲的哥哥又在土改時被還鄉團殘忍殺害,命運悲苦。
解放后經歷了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在深翻土地壓沙治堿、平整土地、興修水利的勞動中,每天她戴著納得密密實實的墊肩,或掘地或挖河或挑土平田,埋頭苦干。娘是個解放腳,就是那種裹過又放了的腳,小腳趾和第四腳趾是折在腳下的,其勞苦可想而知。那時人民感恩翻身解放,感恩當家做主人,有著極強烈的勞動熱情,每天披星戴月兩頭不見太陽地干,因此我早上起床從來沒見過娘,只有天黑后才見娘沾著一身未干的泥回來,有時還會省下核桃大一點雜面饃帶來,那是她中午發的窩頭,每人倆個,娘惦著我們,舍不得吃完。“三年自然災害”時娘患了浮腫,身上一摁一個坑。1964年是個好年成,但還是多喝糊肚少吃饃。糊肚就是稀飯,灌個水飽糊弄肚子。打紅薯糊肚時娘總是把大塊紅薯舀給我們,攪疙瘩湯時總是把面疙瘩撈給我們,偶爾喝到一豆大疙瘩,也要吐出來喂給弟弟妹妹,回想起便心酸落淚。六十年代后期有了東方紅拖拉機,有了水車,有了人推牛拉的水澆田。七十年代有了機井、柴油機、水泵、電動機,大部分莊稼得以灌溉,鹽堿沙荒變良田,產量逐年增高,到畝產達到八百多斤時,糧已有余,穿戴也因有了合成縴維等代棉品而不再作難,而娘卻突然離世。現今靠良種、水澆、化肥農藥,畝產已過千斤,且連年丰收,而娘卻沒吃的,怎不讓人牽念呢?
老家有糊社火的習俗,就是白事時糊些牛馬車房搖錢樹聚寶盆等,點燃隨葬,經歷“破四舊”也未易除。可那車馬房等好糊,也好燒了敬她,可這沒吃的了,該咋辦?當然能燒紙錢冥幣,可有了錢買不到糧咋辦?我的心緒依然紛亂。冬天回老家,忽然想到國家儲糧,於是托弟弟去紙扎作坊糊座糧倉,糊些五十斤裝的袋子,糊些十斤裝的陶罐,寫上大米白面五谷雜糧各十萬袋,油鹽醬醋等各十萬罐,放置倉內,清明前給娘敬上。
俗話說清明麥埋老鴰,埋為遮掩意。現下暖冬,麥苗起身早,清明時可比老鴰高多了,綠油油的,隨風翻波涌浪,一派丰收在望,這么好的莊稼,怎能叫娘沒吃的呢?走在回家祭母的路上,我還在想。
至娘墳前,弟弟擺好那個“放滿糧油的倉房”,我們磕頭跪拜,焚燒敬上,了卻心事。我不迷信,實為日思夜夢之心弦事。至於“十萬”之數,并非為了奢侈,娘不光仔細,還善接濟人。仔細也是俗話,節儉意,娘會接濟別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