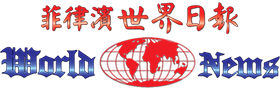第12版:廣場

本版標題導航
日期
當前報紙日期: 2019-04-26
我與養父
彥火
2019-04-26
父親與派克墨水筆
我有二個父親三個母親。
第一個父親是在閩南家鄉的親生父親,另一個是在菲律賓的養父。
我的第一個父親在我出生之前逝世。我的母親年屆四十歲高齡才生我,大抵認為我剋父──是不祥之物,便把我賣給外鄉的一個菲律賓的僑眷。
我現實生活中的父親,只有養父一個,以下我寫的父親也是指養父──
屈指一算,父親已去逝33個年頭。歲月倥傯,雜務纏身,彷彿離我上次去拜祭父親的時間,也有20年了。但對父親的思念,卻沒有因為時間的遞增而稍減,待到父親忌日這一天,壓迫得我喘不過氣來。我想,我無論如何應該抽暇去遙遠的州府(閩南語,偏遠山區小鎮)憑弔一下父親。所以特地向公司請了幾天假期,跑一趟菲律賓。
父親十二歲時被他叔伯帶到菲律賓做零活,自此後長年累月在菲律賓打工、生活,二十歲出頭返家鄉討了養母,小住個把月便返菲。世局波譎雲詭,後來中國解放,韓戰、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全面封鎖,用養母的話是“交通斷了”,自此父母兩地相隔,直到五十年代後期父親才申請我們到香港。
期間因菲律賓政府實行菲化政策,為了在菲做小本生意,父親在菲律賓娶了番母(閩南語,意喻菲律賓土籍女子)。
我與養母一直相依為命。1957年輾轉來到香港,父親跑來香港探我們也不過七八次。父親在生的時候,我與養母偶爾也到菲律賓去探親。每次相聚也不過個把星期,所以在我童年的記憶中,父親恍惚是來自另一個世界,有點虛幻。
長留我記憶中最明亮的印象,是父親送我那一根粗大派克墨水筆。那是我從閩南家鄉來到這個蕞爾小島不久擁有的第一支派克筆。上世紀五○年代,香港市面最流行、也是最時髦的也就是手指般粗、黑地滾金的派克墨水筆。
父親是文盲,雖然他會打算盤,又會做生意,卻連“大”字也不會寫(他的口頭禪)。
寫字當然要用筆,寫好字用好筆,是言之成理的事。結果,在新年,十歲的我收到父親的禮物──一支派克墨水筆。
我打從懂得寫字開始,便沒有好好地練過字。一旦握著一支名牌筆,大抵是心情緊張之故,手顫得巍巍乎,寫出的字更歪三倒四了。
父親從來不看我寫字,我也從來沒有告訴他我用上派克筆之後字寫得不好。他是以為會寫得好的。
有一次,他還向朋友誇耀他買了一支好筆給我。
這支筆最終的命途怎麼樣了,我怎麼也記不起。以我的習慣,我是捨不得丟掉舊物的。只要是我觸摸過的,油然有一種感情在,丟掉舊物,彷彿丟掉一份感情,總是依依。
使我感到愧疚的是,雖然年幼的我便能用上名牌筆,我的字還是不長進。這一點,我是始終沒有告訴過父親的。爾後,我一直不再用名筆寫字。
不少寫稿的朋友也不用名牌筆寫稿,是因為稿費低的緣故吧。
名牌筆的意義是用來給大班簽名或佩在身上,作為身份的象徵。我之不用名牌筆,是我拿上名牌筆便有一份心理的壓力。
我曾收到過一些朋友餽贈的名筆如刁彭、萬寶龍等,我是毫不遲疑地轉送給朋友。我較早用的是斑馬圓珠筆,當初是兩毫子一支;後來水筆面世後,便一直用雜牌細水筆。這都是最廉價、卻最頂用的筆。
一角斜陽不分古今
三十年來,我用廉價筆塗塗寫寫,出版了二十多本集子。這一點,我是始終沒有告訴過父親的。
許多年了,有一天在菲律賓南部小海島與父親敘晤,看到父親灰白的鬢髮和滿臉的皺紋,情狀如老舊派克筆滿佈金邊的條條坑坑,便戰戰兢兢地想起父親給我的筆。
船臨啟程了,送船的父親戴著一頂草帽,微駝著背,一逕向我揮手。我的視線模糊了:父親的身影漸遠漸小。我因而曾下決心要告訴他送我派克筆和我寫字的事。
30年前,最後一次見到父親。父親因中風躺在宿霧醫院的病床上,鼻孔插著兩條輸送葡萄糖水的管子。
彼情彼景下,我已忘記我要告訴父親的事。
又有一個年頭,我老遠跑到那個小海島去拜祭父親的墳墓,我在上墳香的時候,終於告訴他,我沒有用他給我的派克筆寫好字,而且我還用廉價筆塗了二十幾本集子。
又過了好幾年,我坐在書桌旁,用廉價的水筆寫了這篇小文,獻給在天國的目不識丁的父親。逾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了,我發現,我對此一直未能釋懷。這就是為什麼我最近又再跑一趟菲律賓。
父親住在一個小島上,英文名叫Palompon,我自己翻譯成“拔琅邦”,是禮智省(Leyte)一個小鎮。
早年香港到宿霧沒有直航機。從香港去拔琅邦首途要先取道首都馬尼拉,再轉機到第二大城市宿霧,然後再在宿霧碼頭乘一夜船,翌天凌晨五時許才到達。
由宿霧赴拔琅邦是客貨兩用船。分樓上和樓下兩層。上層放置一排排帆布床,樓下主要載貨,從宿霧辦的貨物,從糖果、油鹽、柴米到化妝品、針線,從拔琅邦去程則是椰乾、木材、山貨、乾貨等。
我們大約在晚上八時許上船,船要在十時許開。船上沒有空調。登船要帶備一把扇子,船未開時很翳熱。扇子在這個時候大派用途。
船啟錨,船員把懸在船舷的帆布放下,海風往往把帆布刮得獵獵作響,令人難以安眠。
當年乘搭這種客輪時還不知有風險,直到多年前弟婦與大侄女乘搭的客輪,在途中遇到強烈的風暴,整艘客輪沉沒,全船連弟婦三百多人罹難,才知道這一程夜航的險讞。
想起老母親對我說,父親因是文盲,所以特地跑到那麼遙遠的小島去尋活計,不禁黯然。
我這一次從宿霧到拔琅邦也有多一項選擇,可以從宿霧乘搭二個多小時快船到另一個城市旺木(Ormolc),再由旺木乘搭二個多小時的麵包車去拔琅邦。
至於赴拔琅邦的客輪已趨現代化,上層有雙架床,有裝設空調的商務艙。這次我來回選擇了不同的途徑,但是,每登上客輪,想起弟婦與大侄女的慘死,便心有戚戚然。
我去程選擇取道旺木,上午十一時許在宿霧起程。因在旺木呆了兩個多小時,到傍晚才到拔琅邦。
眼下的拔琅邦已今非昔比。過去只有一條揚塵的主街道,現在已多了好幾條大街,熙熙攘攘,街上擠滿了三輪車。
種根拐杖也能長
菲律賓有千島之國美稱。她由浮泛於太平洋上七千個小島組成。深入菲律賓腹地,是大異其趣的。這裏民風淳樸,景致幽雅,尤其是一些閩南人稱之為“州府”的山頂,大都是在蓊蓊郁郁的椰樹簇擁之中。一條揚塵的泥沙路,傍著幾爿唐人舖頭或菲人舖頭,四邊作扇形分布的是櫛仔厝。而鎮頭鎮尾大都枕著一泓湛碧海灣和婆娑的椰樹林。
徜徉在這樣的一個小天地,紛繁的鬧市聲已漸遠去,放眼是藍天碧海和蕉風椰雨。你可以撒開雙腳在軟綿綿的沙灘留下紛沓的足印,或在滄波白浪間載浮載沉,渴了可以嚐到剛從椰樹摘下的沁人心脾的鮮椰子汁,餓了可以大啖濃甜的菠蘿蜜。
菲律賓地處火山地帶,泥土黑肥,雨水充沛。父親說,上天對菲人太好了,在菲律賓隨便插一支拐杖也能生長。這未免誇大其詞,但是菲律賓的天然資源之豐厚,卻是不爭的事實。
菲律賓地屬熱帶,白天熱氣迫人,但是每天傍晚都會下一場驟雨,暑熱驟清,晚上涼快得多了。
菲人種植十方簡便,有點“刀耕火種”的味道:放一把火燒掉雜草,便可以下種,因每天傍晚都有天然雨水灌溉,不必太費心照拂,便可以坐待收成了。
菲律賓華人大都是早年從閩南山區遷徙過來的。閩南大多是石頭山,土壤呈赤紅色,只合種植地瓜、芋頭等粗糧,還經常鬧饑荒。
菲律賓華人的奮鬥精神,恍如菲島孤高卓絕的椰樹,足跡遍及浮泛在太平洋的七千個大小島嶼,從繁華的大都市到窮鄉僻壤,都有一頁他們用血和汗澆鑄的可歌可泣的歷史。
老父在那個有點荒涼的小鎮拔琅邦落腳,前後歷經一甲子歲月。記憶中,那裏沒有酒樓,只有“饅頭爐”(麵包店);沒有夜總會、舞廳,只有露天的民間舞會;沒有電影院,只有有限的幾架電視機收看來自馬尼拉、宿霧的電視節目。這裏的娛樂場所,只有一間簡陋的鬥雞場。
這裏沒有城市慣有的繁華、現代化,卻有自然的淳樸村野風味。都市的人很難想像可以在這裏呆上一輩子,但老父卻心安理得地渡過他的青少年、中年、直至老去。
滿頭白髮的老父,從來沒有想到離開這塊土地,他將全部的青春獻給異國的土地。
他也來過香港好幾趟,但繁華的都市生活,卻使他感到不安和困擾。他寧願跑回到老遠的地方,在現代文明的背面去過其怡然自得的生活,去頤養晚年,他的生活簡單而寧靜,但他也沒有現代人的苦惱!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