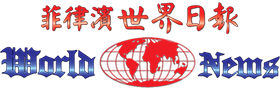第12版:廣場

日期
當前報紙日期: 2019-11-13
路在腳下
宇文芹
2019-11-13
西諺“條條大路通羅馬”,但關鍵是有時沒有大路,甚至還沒有路。改革開放初期,我要穿過田間崎嶇不平的羊腸小路,到大隊小學去上學。每到農忙季節,田埂上不是農肥、秧把、泥草,就是麥捆、稻鋪、老牛……擋住了去路。記得有許多次我是從迎面挑擔而來的農人擔下鑽過。有時田埂上有缺口而滑入農田,或一腳滑入水田弄濕衣服和書包的情形時有發生。有時路上還會遇到蛇和田鼠,農家的孩子大都是不怕的,我還敢用手提住蛇的尾巴和掐住它的頸部,讓它俯首稱臣。但少數丫頭們膽子小,見到它們就嚇得哇哇大叫。最擔心的就是暴雨天氣,田埂與農田全被淹沒,分不清哪是路哪是田,要赤腳淌水,“摸著石頭過河”探路。
隨後,我去更遠的鄉中學讀初中,徒步單趟要一兩個鐘頭,只能早出晚歸,午餐在學校食堂解決。有回下雨,我們不懂事,從農人家剛剛碾平的麥場直接踩過去,把人家辛辛苦苦弄平的場地踩出一排大坑小氹的,遭到了人家半個多小時的攔截。
九十年代初,走上工作崗位,有幸被分配在離縣城不到10公里的農村中學任教,由於家住縣城,所以每天騎著自行車早出晚歸。八波鄉中學地處城北丘陵區,雖然也崎嶇不平坑坑窪窪,但因其上鋪石子,雨天不怎麼泥濘,可以騎車行駛,總比當年我上學時陷入泥塘好多了。我曾懷疑“八波”是否應為“八坡”?因為從家到單位正好要翻越8個大的陡坡。下坡時總是很舒服,坐在自行車上,不費吹灰之力地自由落體地滾下去,可是上坡就沒那麼容易了,往往沒騎過一半,就要下來推車前行。我剛到單位時,有位老師打趣地說:“我們的敵後小分隊又增加一位新成員了,歡迎你加入。”他的話很突兀,當時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沒明白他話中的意思。由於路面不平,所以經常車胎被戳破,只好扛起自行車前行。直到上世紀末,路面改造成瀝青,才得到好轉。在八波工作十來年,騎壞了四五輛加重永久和鳳凰牌自行車,補胎無數次,終於迎來了平坦的柏油公路。
要想富,先修路。新世紀,“村村通”工程實施時,我就回城裡上班了,未能親眼目睹那番天翻地覆的改造,但卻有幸回了祖籍合肥。
十數載前一個清明節,忙中偷閒,又加上老母親的嘮叨叮嚀:人不能沒有血緣情,更不能忘記自己的祖宗。於是聯繫到朋友的一輛車,多少有些虛榮和炫耀,仿佛高祖衣錦還鄉一般回老家掃墓了。行完了省縣幹道,桑塔納轉到去鄉村的迤邐土路,便顛簸抖動起來,儘管司機是個車技高駕齡長的老手,但額頭也冒出了串串汗珠。實在不行的路段,車裡的我們乾脆下車,只留司機師傅與車一起蠕動。不好,只聽見“嘎”地一響,底盤低的車,在離村莊不遠的單塘旁被擱淺了,路上拱起的流水石橋杠到了車底,黝黑的機油流了下來,糟糕!油缸被蹭裂了。屋漏偏逢連夜雨,春雨已把路面淋濕,路變得泥濘爛滑起來。車無法行駛,只能靠我們人推,後來推它也紋絲不動,完全陷入泥濘中,就像那千年的老樹頑固地將自己的根深深地紮入泥土,讓人無可奈何到了極致。面對它,我們真是阿斗當皇帝——軟弱無能。
回來時,在村裡喊人推車,哪來年輕力壯的青年,基本都遠走異地他鄉打工去了,好不容易找到了兩個老實本分的種田漢,又到鄰村請了幾個,大夥幾乎是把車抬到柏油乾路。又請來拖車,拉到最近的修車處作簡單修補,才勉強得以返程。家鄉人打趣地說:你們很少回來,這一回來,老祖宗們都不讓你們走了。
事隔幾載,國家調整節假日,清明有假日,才有時間得以再次回鄉祭奠。前車之鑒,這次我找了輛越野式的本田CR-V,臨行前又帶了兩把大鐵鍬,別人以為多此一舉:大鍬農村多得是,自找麻煩。只有我暗守其中的天機——遇到不好的路段,可以鏟土填凹夯平。青山碧水、黃花綠意,豐饒香甜的田野,一切那樣熟識,一切又那樣陌生:下了省道的鄉間土路再也無影無蹤,取而代之的是一條平坦厚實的混凝土公路,一直向村莊伸展,車平穩地飛駛,似離弦的箭,飛馳的駒,暢通無阻地到達村莊,不再像以往那般以蝸牛之速顛簸前行。
上墳期間,在山崗俯視鄉村,一條條水泥路似白色的飄帶在春光裡舞動,也像一道道銀色的河流逶迤著熠熠泛波,又宛如筋脈血管縱橫交錯,又似蜘蛛網四通八達,在鄉間延伸。“村村通”工程和新農村建設,已使條條大道通鄉村。
時代燃燒了歲月,燒盡了當年的貧瘠荒涼,點燃了如今的豐盈繁華,回首往昔,顧看今朝,驀然發現,幾載年華,卻換了人間。 西寧線高鐵通車了,40分鐘到達省會合肥,半個小時到達南京,向東二三小時到達東方國際大都會上海,向南到達溫州、廣州,向西可到武漢、重慶、成都和西安。
環繞在我們周圍的全是路:滁全路、緯一、緯二……一直到緯七路,寧洛高速、京滬高鐵、揚滁馬高速通車……
從古絲綢之路到一帶一路,路寄託著我們的夢。
幸福是靠奮鬥得來的,路是走出來的,路在腳下不斷地延伸,路也讓我們走得很遠,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