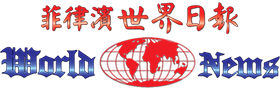蟋蟀在堂,歲聿其莫。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都是詩經裡的句子。“在堂”與“在戶”是同一時間,前者週曆十一月,後者夏曆九月,於我則是公曆十月,就是這幾天。
蟋蟀是有靈性的小蟲,他們一直順著時間移動。有人說,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意思是說三者其實都是蟋蟀,從農曆五月開始,他們就在不斷的變化位置,在野,在宇,在戶,最後入我床下,在淒寒的北風中,息了聲息。
深夜,我的屋內有一隻蟋蟀叫了。
就像在上古的西周裡叫,在龜甲下叫,在生出銅綠的簠盨匜甗邊叫,趴伏在刻著神秘祭文的鐘鼎上叫,伏在發黃的詩經裡叫。它叫了一聲,遲疑著,又叫了一聲,我的室內頓時秋氣漫膝。歲聿其莫,莫通“暮”,年過中秋,桂花落過,歲月忽已晚。蟋蟀,是一年鐘面上,爬成鳥蟲篆的時間刻度。
我與周人隔著近三千年的時間,摘除外物,我與周人幾乎一致,會愛,會感動,會感知節氣的推移,就像三千年前的蟋蟀,依然恪守著基因裡作息表。雖然高樓林立,大地不再空曠,秋風不能恣肆地掃過原野;雖然水泥窒息了許多生靈的呼吸,生物不能以息相吹;雖然遠方的冰川融化,氣候變暖,但它依然感到骨子裡的寒意,它一步步靠近我,在野,在宇,在戶,在堂,終將入我床下。
寂夜裡聽來,那細細的聲音,空曠孤寂,又似是秋風故人來。是去年的那只嗎?去年中秋比今年遲了有半月,中秋後的第二場雨落過,天氣立即肅涼,那個明月之夜,我在窗前,窗外鳴聲唧唧。細看有觸鬚一對,窸窸於窗隙間。仄身入,恰好跳上書頁,窸窸窣窣,猶疑不定,繼而跳下,隱入書架之下。是後,夜夜唧唧有聲。
它是不是還是去年的蟋蟀?是與不是,又有什麼關係呢?江山歲有變化,秋風年年來過,草木枯榮,生靈遞代,是則幸甚,不是則坦然。“有緣”兩字太輕。他日乍然相逢,觸鬚窸窣,我便當做是故人相問。
一年來變化有之,有新交,有故去,有糾結,甚至有過半夜不寐的叩問,但去年的蟋蟀來了,它入我宇,我戶,我堂,它帶給了我遼闊和蒼涼。遼闊的是空間,蒼涼的是時間,加在一起就是蒼茫的人世,人海。這種浩渺讓我原諒了自己,努力,儘力善良,快樂最好,如果不能,那麼也接受秋風吹過山崗。
它在叫著,總是在深夜,它是時間的蟲子。我記得電影《末代皇帝》的結尾處,年老的溥儀來到故宮太和殿,站在龍椅前,一陣時光交錯的恍惚。他走向龍椅,被“紅領巾”小男孩攔住。他說他是末代皇帝,馬上就能證明自己。孩子遲疑著,溥儀從龍椅後拿出一個蟋蟀罐來。這是他三歲登基時,大臣送給他的,他偷偷藏在龍椅後。
小男孩拔掉蓋子,一隻蟋蟀慢慢爬出來,爬到小男孩紅領巾上。他下意識抬頭,發現溥儀不見了。陽光璀璨,太和殿幻影斑斕。
那只活了幾十年的蟋蟀去了哪裡?
世上哪有那麼長壽的蟋蟀。
我要善待每年靠近我的蟋蟀。
Previous
N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