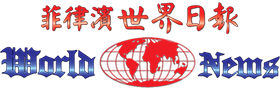第一次進葡萄園是在冬季,那時寒風還在嗚嗚地吹著,打在人臉上猶如刀割。表弟的葡萄園有十來畝地,在冬日灑了一地的陽光下,土地開裂著,一棵棵葡萄樹瘦骨嶙峋像枯死的樹枝,倒在地上,或趴在鐵絲架上冬眠,一點生氣也沒有。我看看一根根不帶一片樹葉的葡萄藤,孤獨得讓人心酸,細若手指,即便是樹幹,粗的也不過手腕粗細,一根根皮包骨頭,乾裂著,皺縮著,核桃殼似的。
表弟是這方圓十裡八鄉種植葡萄的能手,正如城裡的人想出來城外的人想進去,我們互相欣賞著,他景仰我正如我羡慕他。他羡慕我通過讀書進城工作,有知識有文化;我欣賞他肯勤勞吃苦,通過一技之長走上了富裕路。他正在田裡施肥,看到我來,顯得非常高興和熱情,寒暄了一陣,說:“你來得不是時候,明年夏天葡萄成熟時節,你來,可以吃到葡萄,還可帶些回去讓姑媽和姑爺嘗嘗。”我乜斜著旁邊東倒西坍的所謂葡萄樹,不敢恭維,也不信這乾巴巴的、毫無生機可言的僵死葡萄樹能生長出什麼果實來,頗有些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不屑,但還是客氣地說了聲“謝謝”。
表弟似乎看出了端倪,拉了根似乎枯敗了的葡萄藤讓我折,我想枯死的樹枝折起來嘎嘣脆,孰知拿在手裡無論怎樣蹂躪都不斷,把它的皮弄破,竟溢出青綠的汁液來,原來它不是枯死的,而是熟睡在寒風中的精靈。它太柔韌了,韌性超出了我的耐力,最後還是以我失敗而放棄。事物不可貌相,我對它的成見有所改變,但還不全信它能孕育出多少甘甜可口的果實來。暗地決定明夏一定再來,不是為了一飽口福,而是為了證實一種看法。
葡萄成熟季節,我如約而至。在我眼前展現的是一片碧海,那鬱鬱蔥蔥生機勃勃的葡萄葉,在與夏日的驕陽嬉戲挑逗,為一串串晶瑩玉潤的葡萄打著綠傘,蓋著厚密濃實的綠毯。走在泱泱綠意的葡萄園裡,鑽在葡萄架下,真不敢相信,藏在葡萄葉下的是蔓延著的葡萄樹藤的子女們,它們簇擁在一起形成串,一串串沉甸甸地倒掛在架上,瑪瑙似地紅著臉,姹紫嫣紅的,像一個個充盈的氣球,正朝你笑。表弟說,一棵葡萄樹結的葡萄有幾十斤乃至上百斤重,不是眼見,哪敢相信那一根根細莖藤是怎樣鍥而不捨地將根須紮向大地深處,汲取生的甘泉,輸送多少養料,長成了葡萄的甘甜。它們似母體的臍帶,孕育著子女,把自己的希望與理想高掛枝頭。又像一根根牽掛風箏的線,當葡萄成熟時,就放飛它們。
我不再藐視那粗陋枯乾的葡萄藤,它並不淺薄,更不醜陋,而透著一種骨子裡的美,美到極致。那盤曲的虬枝是絢爛後的寧靜致遠,是鉛華洗盡後的樸真。是它們孕育了如此濃密的綠色,成就了如此甘甜的果實。我忽然明白:粗陋能孕育出美麗,偉大寓於普通。
Previous
N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