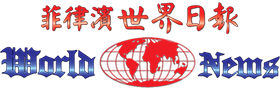故鄉樅陽屬皖中,傍依長江,緊臨安慶,是四季分明之地,冬天雖然沒有真正的北方張揚,但也是冷得棉襖棉褲棉鞋齊上陣了仍直打哆嗦,偏偏還不能名正言順地享有暖氣。所以在過冬時,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聰明的人們便用上了火桶、火球等物品以取暖,好度過漫長而寒冷的冬季。即使是在難挨的饑荒之年,冬日裡也是沒有一家會讓火桶缺火的。溫飽溫飽,先溫後飽,火桶,它不負期望地為那貧寒的冬日輸送著陣陣暖意。
一般的火桶,是請木匠用一些跟凳子差不多高的木板圍成的中空的圓形桶,再從外部用鐵環或者竹蔑箍緊實。舊時的火桶外形下部細些,上部略粗。火桶裡面要放入掏好火的火鉢子。火鉢子一般是陶制的臉盆大小,掏火前火鉢子裡放上松果子、木屑等。當時的鄉下人家都燒柴火鍋,飯煮好了,將灶裡頭未滅的柴灰掏到已放好松果、木屑的火鉢子裡,稍稍壓緊實,再放到火桶裡,放上鐵製的或者木製的隔熱蓋,一切便都準備妥當了,人就可以坐到火桶裡了,搭上一件蓋腿的舊布襖子,不一會兒,便覺寒冬不再,暖意四起。
作為掏火時放在火鉢子裡取暖的底料,松樹果子自然是首選。既不用花錢,又耐於熬火發熱。
所以,為了陰冷缺太陽的冬天掏火時有足夠的松果子作儲備。在每年入了秋後,一到週末,村子後面的桃花山就成了我們一班差不多大孩子的樂園,我們幾個會一起拎著蛇皮袋,到山上撿松果子。松樹的果子熟透了的會自然脫落掉到草皮上,所以開始時我們一個個拾撿得很是輕鬆,大家會比賽似地拼著眼疾手快,待到三人中有人拾滿了袋,就開始幫助沒有完成任務的人,地上松果子畢竟有限,撿光了後,我們便尋起了樹上的,樹矮的,直接伸手可摘。樹高的,就叫力氣大些的小夥伴扶著松樹使勁搖,讓未撿滿袋的人撿了回家向大人交差。做這樣的差事,論眼疾手快是沒有人能比得過娟的,怎麼誇娟的勤勞能幹呢?就像現在的孩子比成績,每個孩子的童年裡都有個媽媽口中的別人家孩子一樣,娟於童年的我來說,就是這樣的存在。我的溫吞散漫的性子與娟的利索形成了強大鮮明的對比,忙不停歇的母親是多麼希望她也能有一個像娟一般能幹的女兒呀,可以幫著她分擔一些家務,讓她也有可坐著歇歇的時間。所以她對我常有恨鐵不成鋼之意,卻又無可奈何,用現在流行的話調侃:誰叫是自己親生的呢……
冬日在火桶裡打牌也是極好的。圓的火桶,周圍放四張差不多高的方凳子,四個小夥伴一起坐下,四膝相抵,緊密無縫,像張小桌子,再在“小桌子”上面平鋪件家裡不用的舊花布襖子,一來捂暖,二來放牌,也有講究些的時候,再在花襖子上放個竹篩子用作放牌,更是完美。如此一切準備妥當了,便開始了冬日裡要麼一上午要麼一下午的牌技大比拚,也沒什麼賭注,也無輸贏獎罰,玩的也是再簡單不過的鬥地主,打烏龜,或者直接玩接龍比大小,卻玩出了無窮的樂趣。火鉢子裡厚厚的柴火灰掩蓋下的松果子一點點地被引燃,在緊實的灰燼下散發著恰到好處的溫熱,透過媽媽們納的千層底布鞋,直暖到心窩裡。這是孩子們的樂子。
至於忙過了春夏秋三季的鄉里婦人們,在清閒的冬日,一個人或者三倆要好之交一起坐在火桶裡打毛線衣、納鞋底、釘鞋幫子,或者縫補衣物,一邊做事一邊閒聊,家長裡短裡不亦樂乎的勁頭似乎一點兒也不輸我們這些孩子。
火桶還有一種作用是保溫,冬天裡往往一個菜燒好了,前面燒的菜已經涼了,所以放在火桶裡保溫是非常好的。還有拿來烘衣服鞋子的,趕上下雪天,皮孩子們玩雪玩得棉衣棉鞋濕了,換下,臨睡覺前,家裡大人會把脫下的衣服鞋子放在火桶裡烘乾,有時早上起來衣服還是溫暖著的,穿上舒服極了。
而火桶最顯地位崇高的應就是作嫁妝時了。小時候,誰家有女兒要出嫁,就會提前請村裡手藝好的木匠師傅到家裡,早早地箍個火桶,待得女兒出嫁當作嫁妝與其它物件一起陪嫁到婆家。油漆得光滑鮮艷的火桶裡面,會和陪嫁的棉被裡一樣,放著染得紅彤彤的花生、桂圓還有紅棗等,寄託著娘家人對嫁出的女兒最深的期望:希望新人日後的日子過得紅紅火火。
去年冬日最冷的那幾天,在我常潛跡的E網群裡,見得南京文友萱草幽幽抱怨:冬天,還有什麼比床更愜意的地方呢?當時很直覺地脫口而回:火桶呀,一杯茶,一本書,一個火桶,比床可愜意多了!
火桶——這個自我嫁來閩南近二十年少有接觸甚至基本未有機會提及的舊物名詞,它就那樣自然地浮於腦海,脫口而出。同時生發的,還有在時光深處的和火桶相關的所有記憶。那些記憶蹚過三十幾年的時光之河清晰如昨、鮮亮如昨。那些壓得堅實的草垛,依著草垛的火桶,童年的我們依在火桶裡快樂地嘻戲,身上沐著溫和的陽光,腳下是松果在壓緊的柴火灰燼下慢慢散出的溫熱,那些明明清貧得只剩下孩子滿臉無憂的笑,卻都美成了記憶河裡愈來愈鮮艷的畫,如此令人懷念。
我不禁設想起許多種在舊時光裡走散的我們他日別後重逢的情景。最好是冬日吧,在桃花山下,草垛旁、火桶邊。最好是邂逅在冬日的午後,只要一個微笑,連問好都顯得生份,掀起舊棉襖的一角,挪開些位置,把腳放進火桶。
還有什麼,比這樣的促膝相逢更好呢?也更暖吧。
Previous
N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