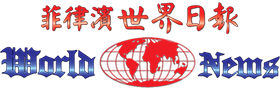李國文,是中國大陸的著名作家。1930年生於上海,祖籍江蘇鹽城。1952年曾赴朝鮮戰場從事寫作,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1979年重回文壇。1980年,其短篇小說《月食》獲得該年度“全國優秀小說獎”。及後,其長篇小說《冬天裡的春天》、中篇小說《涅槃》、隨筆《大雅村言》相繼獲魯迅文學獎,長篇小說《花園街五號》更曾被改編成電影和電視劇。此外,《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一書獲得2003年華語傳媒文學大獎。他曾榮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主席團委員。
說句心裡話,筆者很喜歡李國文先生的作品,至今購有他的多部作品,包括《中國文人的活法》(2004年3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大江東去》(2000年10月,由廣東出版社出版),《李國文雜文》(2006年9月,由中國社會出版社出版),《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2002年4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李國文說唐》(2006年7月,由中華書局出版)等。
讀李國文先生的著作,筆者被其淵博的知識、優美的文筆所折服。但是,在閱讀的過程中亦發現一種現象,他很喜歡以不點名的方式拿當今的中國文壇和某些文人“開涮”。這種“冷諷熱刺”指責社會現象,並不針對任何特定對象。
口說無憑,舉例為證:
“反觀近來那些口出狂言,以為語驚四座,(與李白)相比之下,恐怕只能等於陽痿患者的偶爾勃起的小意思。”(《大雅久不作》)
“時下,偶爾出現的,那一些要往地毯上吐痰,一定要從窗口向外撒尿,一定要從摩天高樓上往下擤鼻涕,一定要隨手牽羊從賓館順走些什麼,一定要吃約稿女編輯的豆腐,甚至動手動腳,一定要住星級酒店不然就會失眠,一定要有左擁右抱的三陪小姐才會詩興大發,一定要麻將打到天亮眼珠通紅走出房間的文人,相對於古人的表現來說是小小不言的無行了。”(《文人無行》)
“去年,加上前年,好多德高望重,以及德並不高,望也不重的名流組合,開始熱衷於總結20世紀的中國文學,紛紛進行一種《封神榜》的封神運動和《水滸傳》聚義廳裡排座次的遊戲,真是好不熱鬧。”(《“文章得失不由天”》)
“這些年來,一些很一般的作品,不照樣弄到地動山搖的程度,如今今人當真寫出一部類似《阿Q正傳》的劃時代作品,落入一位炒作家手裡,要不鬧出七級地震那樣大動靜,是絕不會善罷甘休的。”(《“文章得失不由天”》)
事例不勝枚舉,因篇幅關係,就止打住。
從文中來看,今時今日的中國文壇很是“熱鬧”,怪象叢生。
魯迅先生曾寫過一篇雜文《辯“文人無行”》,他感嘆道:“輕薄、浮躁、酗酒、嫖妓而至於鬧事,偷香而至於害人,這是古來所謂‘文人無行’”“為了防後方,我就得橫站,不能正對敵人,而且瞻前顧後,格外費力。”“死於敵手的鋒刃,不足悲苦,死於不知何來的暗器,卻是悲苦。”
李國文先生對魯迅先生的話,毋庸諱言,頗有同感。他在《最難描畫文人臉》一文中,說:“文壇,有的時候,挺像一場假面舞會。你見到了,但實際不是你想看到的臉,你跟他握手,但你不知道到底握著誰的手。你握著對方的手了,但你也猜不透另外一只手,握著的是快刀,還是鮮花。”又說:“三十年代的文壇,已是歷史,五十年代以後的文壇,我是親身經歷過來,文人之對於文人,其實是最不相容的。儘管面容很親熱,握手很給勁,但到算計你的時候,下刀子是一點也不手軟的。直到今天,我七十有餘,對儕輩還是不能奢言了解二字。”
毫無疑問,李國文先生之所以產生如此觀感,與他在五十年代的“反右運動”和六十年代“文革”的遭遇有莫大的關係。他在《曹雪芹的苦惱》一文中透露道: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政治運動,比較文明。聲嚴色厲是有的,痛批猛揭是有的,但動手打人,令被運動者受到皮肉之苦,倒不多見。至少1957年打右派時,雖說右派是“打”出來的,但鄙人大會小會熬了過來,倒不曾挨打。被唾棄者唾沫星子濺得我臉上開花,是有的;被揭發者狗血噴頭嚇得我目瞪口呆,是有的;被義憤填膺者搞車輪大戰,罰站得我昏昏欲倒,是有的;但托上天的福,倒沒人碰過我一指頭。到十年“文革”期間,就完蛋了。說是“文革”其實倒是結結實實的“武”革,真是“幾度疑死惡狗村”啊!至今,我的肋骨在X光片裡,一邊高,一邊低,就是那場革命留在身體上的“勝利成果”了。
寫到這裡,筆者不勝感慨: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於今尤烈。
Previous
N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