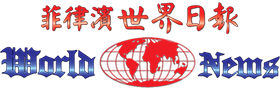母親離開我們、走了,家門口一槃老磨就成為我思念母親之情的寄托。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村是遠近聞名的“豆腐村”,做豆腐是村裡一項比較普遍的小副業。村裡人想掙點薄利彌補家用,天天起早摸黑,挑燈推磨做豆腐。推磨發出的吱吱聲與狗叫聲此起彼伏,打破黑夜的寧靜,散漫在村莊空氣裡,沉積在幾代人的心坎上。
那時候,我家裡有一槃石磨是一位做石雕的堂叔無償贈送的。在那困難時期有了一槃石磨就意味著多了一條出路、多了一點收入。自從有了那槃石磨,母親就與鄉親們一樣日挑水、夜推磨、浣衣燒飯、出工下田,撫養子女,整天忙得像石磨一樣團團轉。
推磨磨豆腐是一種苦力活,需要力道和技巧的結合,更需要兩個人的默契配合。一個推磨、一個投料,推手扎穩弓步,雙手握緊用繩子掛在頭頂鐵?上的丁字形推柄橫杠(籠?)兩端,以扭腰送胯之合力向前推出,石磨按順時針方向轉動,豆漿便從那相合面的齒槽裡源源不斷地淌下。送料手就站在石磨旁,眼隨磨轉、手隨眼動,看見上扇磨的磨眼空了就在石磨快速旋轉中,瞧准機會,把溼泡好的豆和水按一定的比例准確無誤的灌入磨眼,其精准度不遜於“賣油翁”。可是,那些年我母親始終是獨自一人忙碌著。她以其孱弱的肩膀頑強撐起一個貧窮的家,讓我們一家人渡過了難以忘懷的艱辛歲月。
一槃石磨的質量直接影響著磨豆腐的速度和效益,磨槃上下凹凸對稱吻合、相合面齒紋均勻對稱鋒利,出漿多、質量好、效益高;反之、費時費力又費料。好磨出好漿,加上母親的精心制作,做出來的豆腐水嫩嫩的,好吃又好看,當然也好賣。
如今隨著人們生活不斷的改善和技朮的進步,磨豆腐的傳統行業逐步走向專業化和機械化,石磨作為一種原始的勞動工具,即將隨著一代代人的淡忘塵封在歲月裡。偶爾想吃一口母親做的豆腐已成為一種甜蜜的回憶。睹物思情,逢年過節一家人聚餐在一起,餐桌上菜肴裡的每一塊豆腐都格外親切,不禁勾起兒時的記憶,總有一番滋味涌在心頭……
一切存在過的東西都有它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最近幾年,一台台零落在村間老屋殘牆斷垣邊破舊的石磨,不經意間重煥新生,一些閑人雅士把它視為古玩,敏銳的商販紛紛來到村子裡,以一至三百元不等的價錢向村民收購。就這樣每當有商販到來,母親整個人就好像變了樣似的,嘴裡念念叨叨、甚至有些坐立不安、還時時拿眼望望我。雖說知母莫如子,而我因為感悟遲鈍,一次次被我疏忽掉。直到有一次我悄悄地跟著母親的身後走去舊厝,看到她神情黯然地注視著放在老屋殘牆下那台舊石磨,頓有所悟:母親對老磨溢滿溫情的眷顧,有一種難以割舍的情懷。於是我動員家人一起動手把舊石磨搬到新厝的庭院裡,在鮮花和綠草的襯托下形成一道亮麗的庭院景觀,靜靜地陪著老人家安安心心地走完最後的人生旅程。
歲月悠悠,母親守望著飽含深情、飽經滄桑的一槃老磨,是晚年心靈一種慰藉,同時也是守護著一個家庭永不失落的精神財富和“無字”家訓。亦是“有了一槃老磨的守護,才有了村莊清水一般的歲月”。
Previous
N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