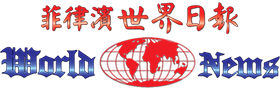冬至都過了好多天了,餐桌上卻仍未見到冬筍的影子。往年這個時節,冬筍已是屢見不鮮了。妻從菜市場回來,說今年久旱,竹子都活得異常艱難,好多都枯死了,還談什麼筍?妻說得也是。可如此一來,我就不由地要憶起我的四哥,以及他挖的冬筍了。
四哥當年不好讀書,放了假喜歡往山上跑,暑期砍柴,寒假挖筍。吃過中飯,母親拾掇好四哥的午餐,就囑我往深山裡送去。烈日炎炎,我頭戴草帽,手挎竹籃,一個人寂寞地朝大山邁去。兩腿無力時,我就納悶不解了:這麼毒的天,還去砍柴,四哥他們不熱嗎?
就在我邁不開步時,四哥他們卻不期然地從彎道里逐一顯現了:三四板車,沿著小道,嘎吱而來。
四哥他們砍柴,向來都是三五成群,鮮有單打獨鬥的。深山砍伐的艱辛,促使他們必須學會通力合作。我迎上去,他們停下來。四哥為人豪爽,見我送飯來,忙招呼大夥過來吃兩口。這時,他們亦不推辭。籃中食物,瞬間就被他們瓜分淨盡。待他們去澗邊飲水回來,我早己將碗筷洗刷乾淨,並於板車上安置妥當了。
四哥他們弓身起步,我則緊隨其後,手推柴車,助四哥一臂之力,逶迤而歸。
寒假挖筍,要比暑期砍柴安逸些,至少是無須負重拉車了,四哥便不用我送午飯,他帶幾隻山芋或是一兩個粽子便可對付過去。歸家的辰光,倒是相差無幾,均是鳥歸巢、雞迴圈、家家戶戶生火造飯的光景。這時,若是還不見四哥人影,母親便要囑我到村口路邊去望一望,看看四哥回來了沒有。常常是我還沒出村口,四哥便肩扛鋤頭背背竹簍,一身泥土滿臉汗漬,風塵僕僕地從村口出現了。
四哥大我兩歲,卻高我一頭,孔武有力,教人一看,就是個硬實的後生。我家兄妹六人,唯有我文弱無力,卻也因此逃過了很多艱辛。四季用柴、傢俱用料,都是幾位兄長從深山裡肩扛車載而來。這當中,四哥出力應是最巨,在我心目中,四哥就是我家的第一等功臣。然而,卻從不見他居功自傲,倒頗有些將功贖過的意味。
什麼過呢?就是學習不夠用心,成績不夠理想罷了。在他面前,我唯一值得被肯定的就是學習比他用功,比他自覺。四哥上山砍柴挖筍時,我則大多是呆在屋前溪邊,洗碗洗筷洗襪子。亦僅此而已。
我總覺得,當年該我受的那份艱辛,全被他代勞了;而該他享受的那份安逸,則全讓我獨攬了。
母親見四哥進了院門,忙伸手將四哥的小背簍從他背上卸下來,說句快去洗洗,便低頭朝簍裡瞧了瞧,然後將簍口朝下,大大小小,完整與不完整的冬筍,便盡攤一地。母親將那些缺胳膊少腿的殘筍、破筍,悉數取出,拿進廚房,留下品相好的,第二天拿去換錢。
等到四哥換洗一淨,餐桌便多了碗味美可口的冬筍炒肉片;若是殘筍不多,母親便會切些豆腐放進去,照樣也是一掃而光。家人聚桌而食的當兒,四哥從不表功,亦不訴苦,甚至連桌都不上,依舊是不言不語地吃他的飯。故而,他山上的艱辛,我們一無所知,只知道冬筍炒肉片好吃,好吃,真好吃。
當然是好吃了,大畫家吳昌碩就有詩云:客中常有八珍嘗,哪及山家野筍香。而四哥挖的野筍,就成了我年少記憶中的珍饈佳品,其味美,堪比母親的烤蹄膀。
Previous
N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