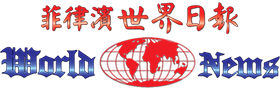當截句詩成為現代詩創作中的一種新樣式而廣受追捧時,台灣倡導先鋒白靈兄一邊以身作則地創作,一邊使盡渾身解數開展活動,他在截句書寫中也不忘以截句論截句。請讀《當截句載著我》:「世界是一面鏡子/我們站在鏡外 或鏡中?//截句飛入鏡裡又飛出/背後起落的 是紅塵?」截句詩並非風花雪月式的隨意句落,而是根置紅塵人間的生命感悟與世事體驗。
白靈另一首論截句詩是《人生也需要截句》:「被雨聲摟著說了一夜話/窗上的風景都濕了//咬住心頭的名字也是,取出/晾掛陽台上,任風截去」。風截去的何止是陽台上晾掛的夜話與心頭的名字,還有夢中多少無言的淚滴。「截」之妙用,就在於截出全然令人驚喜的詩意。
我則跳脫「截」這個字,來一首諧音的《劫句》:「一顆星,存受不住/億萬年的相思/在空中爆破,你我的/眼中嵌入點點芒燃」。我的另一首《分身術》:「鋸子鋸下的一瞬間/所有的眼睛都吊在半空/鮮血,並沒有流出來/但見一首截句:問世」。以截句論截句,竟然有種截然不同的意念,這正是截句迷人的所在。
寫詩是語言的煉金術,強調的是濃縮的藝術,而非和稀泥、拖泥帶水,把詩無厘頭的寫長,不是本事,而是笨事。既然四行已成詩,又何必拖到八行?若把詩意揭得赤身裸體,已無朦朧的神秘美感。
在智能時代,一切追求速度。截句詩、閃小詩求的即是寸勁的爆發力,一招到位,刪掉多餘的枝枝節節。無論是四行新作,還是截舊作成詩,其結果都是一樣,要完成一首高度凝聚力的詩。截舊作成詩,更是考驗作者的應變能力,就好像畫好了一幅四尺全開的中國畫,卻要截成四尺四開的四幅斗方,並重新落款命題使之成為四幅新作,你說有趣不有趣?
無論你認不認同截句、看好不看好截句、寫不寫截句,截句詩都以其崛起的姿態讓你不得不正視。
Previous
Next